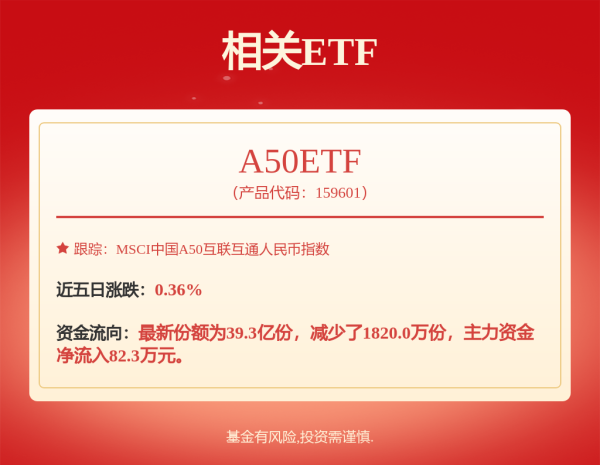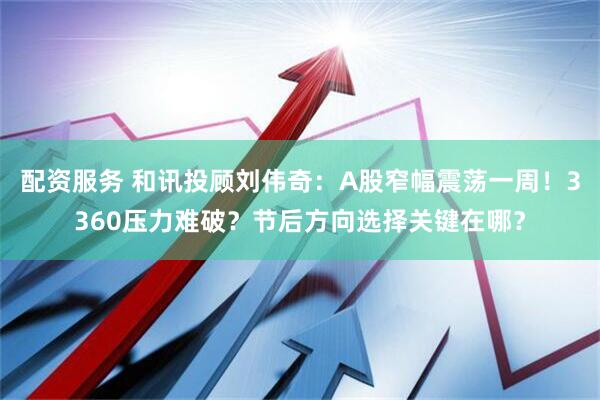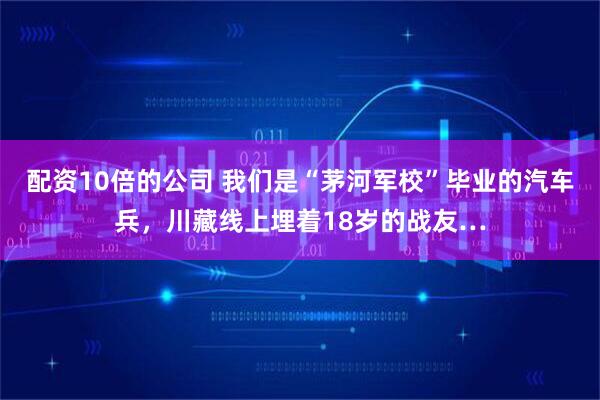
车团军旅配资10倍的公司
一
一九七六年冬天我和大院里的九个伙伴来到川西茅河的一个部队农场,新兵连的战友们俏皮的把这里戏称为“茅河军校”。
川西的冬天寒冷刺骨,我们新兵连住的是农场快要废弃的土坯房。当时的条件很差,我们就用玉米叶铺在地上做垫辱睡觉。
晚上,从墙缝吹进来的风真是寒气逼人,在屋里往上望去能看见天上的星星,下起雨来我们只有收起背包用脸盆接水。

茅河是一个浅丘地带,这里一个个大大小小的黄土坡上松树成林,莺声燕语。
坡与坡之间是农场干部战士开垦的水稻农田,冬天时节没有种庄稼,都灌满了水,到了早上田里结满了冰碴儿。
我们早晚洗漱就在水田里取水…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以老一辈的革命精神为榜样磨炼自己的意志,锻炼自己的思想,用我们火一样的青春投入到训练中去。
我们所在的部队是我军早期组建的一支汽车部队,建团以后长期战斗在川藏线上,在1962年的中印自卫反击作战中出色完成了运输保障任务,立下了战功。
来到这样一支光荣的汽车部队服役是我们的骄傲。
团里特意选派了优秀的干部战士训练我们。
指导员黄照月对我们非常关心,他中等身材,浓眉大眼,一口浓重的江南口音,是团里的一名响当当的优秀干部。
那时的我快满十七岁了,他看我身子骨比较单薄,训练特别辛苦,就把我调到炊事班工作。
训练了一天的战士们饭量特别大,一个班一盆菜,如果动作稍微慢了一点菜盆里就什么都没有了。在炊事班的我们却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
当时我们最兴奋的事情就是希望能看上一场电影。那时的电影是在露天的场地放映的,现在的人们叫它“坝坝电影”。
团里来放映是在农场的厂部,距离我们的住地还有五公里,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我们都有了一定的军人素质,去看电影的路上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口号喊的特别响亮,路边的群众用羡慕的目光看着我们,每一个战士心里无不感到自豪。
二
新兵训练结束我和战友郑海繁被分配到团司机训练队。

汽车部队有条规矩,新兵服役头一两年先做勤杂工作,如炊事员、油料员、文书,通信员等然后才能学技术。于是我们俩来到了炊事班当上了一名“火头军”,尽管这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岗位但是在这里着实学到了很多东西。
班长是个十多年的老兵,大高个山东人对人很温和。他手把手的教会我做大锅饭,回锅肉炒莲花白的香味到现在想起来还直流口水,用大锅下面条看熟没熟用筷子夹起来往墙上一甩,如果能粘在上面说明熟了……
大锅菜肉少菜多,战士们都想多吃点荤,我们给大家打菜时总是想把肉均匀的分配,把勺子里多舀的肉抖下来,当然也有“手下留情”的时候。

那时的城镇兵在部队只是凤毛麟角不是很普遍,人们总认为城镇兵都是导弹(捣蛋)兵,调皮不好带,全团上下用一种特别的眼光看待着我们。
然而,城镇兵绝大多数是有理想有素质的年轻人,他们在保卫祖国的各个岗位上积极努力、默默奉献,为部队增添了新的活力。
分配到九连的朱名江战友在工作中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不怕苦不怕累,工作处处走在前面,因表现突出被评为全团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
战友任君,吕永明,何曾明、张坚等励精图治精忠报国通过自己努力考取军校提干,一干就是十多三十年,成为我们这批兵的杰出代表……
三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一晃两年过去了我从修理连培训结束回到司训队在修理班工作,从此我和班里的战友们担负起全队几十辆车的维修保养和高原运输教练救济任务,工作非常繁忙。
第一次上高原执行任务是前往西藏的昌都。
全团每个连队有几十辆车,在执行任务时为避免交通堵塞都会分成两个车队分别于上午出发一个下午再出发一个。这次我是上午出发车队里的救济车负责殿后。

车轮滚滚,尘土飞扬,车队行进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浩浩荡荡,颇为壮观。夜晚一串串闪着红色光芒的汽车尾灯成为川藏线上的一道靓丽风景。
二郎山是我们车队遇到的第一道险关。这座山背着太阳的这一面常年阴雨连绵乌云笼罩,山那边则是阳光明媚晴空万里,人们也叫它“阴阳山”。
我们要从阴山翻越到阳山那边去,一路上要经过“水帘洞”、“鬼门关”等很多险关……
这些地方山势险峻、薄雾缭绕,加之道路泥泞、弯急路窄,驾驶员如果稍不留神就会掉入万劫不复的万丈深渊,是一段险象环生极其危险的道路。
有一次我队从高原返回路经这里时,一教练车发生机械事故不慎翻入山下湍急的河里,车上六人全部遇难连尸体都没找回来……
那时的川藏线几乎没有隧道,一路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全是崎岖不平的碎石路、泥泞路、冰雪路等,真是“百步之内有险情,十里之内埋忠骨”,被称之为世界奇路。这些对于汽车兵来讲“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无人退缩,勇往直前,在川藏线上谱写着一曲又一曲的英雄赞歌……

车队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险关终于来到了二郎山顶,放眼望去蓝天白云阳光灿烂,盛开的杜鹃花漫山遍野一路芬芳红遍了整个山脊……
如此迷人的色彩惊艳了我们,上山时的紧张情绪顷刻间荡然无存。
康定折多山海拔4000多米,身体能不能适应高原生活就看能不能在这座山上挺过去。
山上白雪皑皑,急弯一个接一个,道路湿滑不得不让人紧绷神经。经过几个小时的艰难跋涉终于来到了山顶垭口,我摸了一下心脏,又摸了一下脑门,感觉身体没有什么变化,这才松了一口气。
下得山来映入我们眼帘的是美丽宽阔的草原,一条小溪水流潺潺从路边蜿蜒流向远方,山脚下藏族山寨炊烟缭绕,敞放的家猪吃着青草……
这一切就是一幅纯天然的多彩油画,现在这里被人们誉为摄影家的“天堂”。
过了新都桥就进入高原了,高原的景象给人一种孤寂而神奇的感觉,方圆几百公里没有人烟,越往腹地走就越感到安宁寂静,好似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它的声音。天气也是神秘莫测,刚才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就会暴雨倾盆。
我们从川藏线北线前行翻越了一座又一座大山,这些山几乎没有植被光秃秃的,像是一个“不毛之地”。
车队停下来休息,老远处走过来一位藏族老太太,手里拿着转经筒边走边摇。走近时我们和她打招呼:“老大娘你好!”,她好像没听见似的,我们又说了几遍她还是不理,于是我们就问:“华主席你知道不?”,“哈莫狗了(藏语不知道的意思)”,我们又问:“毛主席你知道?”,听到“毛主席”时她立即竖起大拇指“毛主席的这个”……

在场的每一个人无不惊叹,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大山深处一个普普通通的藏簇老人一句汉语都听不懂,但是听到“毛主席”时就会发自内心的赞许,可见毛主席在翻身农奴心中的地位是多么的崇高啊。
夏季的高原仍然寒冷,有的地方鹅毛大雪,有的地方阴雨连绵。这里素有“氧气吃不饱,四季穿棉袄。”的美誉。
车队在翻越海拔5000多米高的达马拉山时遭遇阴雨天气,寒冷的气候冻得我们瑟瑟发抖,狭窄的山路泥泞不堪,汽车行驶在这样的道路上滑过来滑过去,让人捏出一把冷汗。我们挂上防滑链小心翼翼的驾驶,艰难的爬行了一整天才到达半山腰的卡集拉兵站。

这个兵站官兵常年坚守在高寒缺氧条件艰苦的山上为过往的部队服务做出了突出贡献,被中央军委命名为“高原红旗兵站”。
一天的劳盹和紧张的心情加上“饥寒交迫”,下了车两条腿都快迈不动了。
吃完饭找水洗碗,怎么也没找着。这时兵站的老兵指着食堂外面的一个装有沙子的水池说:“这就是洗碗水”,我惊讶地盯着老兵,他又说“这是接的雨水,做饭就是用的这里的水。”,我这才过去舀了一碗。
那时的兵站为汽车兵提供的住宿是一排排像库房一样的房子,里面是用木板钉的大通铺,没有火炕也没有火炉。我们的背包是一张四方形的防雨布把垫的盖的和枕头包起来用背包带捆上扔在汽车货箱里,到了兵站拿下来放在通铺上打开就睡觉了。
兵站的米饭虽然是用高压锅做出来的但吃起来还是感觉像夹生饭一样难以下咽,在高原没有新鲜蔬菜,基本上就是用干青菜、黄豆、粉条做成汤菜油水很少,干部餐也就加个罐头。

第二天上路继续爬山,由于山高坡长有的车辆动力不足上不去,于是只得一个人下车把三角木塞在车后轮下面,车猛的向前拱一点就又塞一次,就这样反复多次直到走过这段陡坡才能正常行驶。
翻过这座山就到昌都了。昌都是西藏的第二大城市,只是当时的城市规模也就是和内地的一个小县城差不多。
四
我团十多个运输连队每年执行运输任务往返高原七、八趟,我们司机训练队也有两趟。每次时间最长的要一个多月,最短的也要十天半个月。
延绵3000里川藏线上雪山巍峨、大河湍急,有21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14条汹涌澎湃的江河,横恒着数不尽的险关狭道。
那时的汽车兵行走川藏线好比“手握方向盘,脚踏鬼门关”,是和平年代没有硝烟的战场,每年都有因翻车、高寒缺氧等牺牲的战友。

战友赵武川在执行高原运输时,突发疾病抢救不及时就再也没有回来,十八岁的花季永远留在了川藏线上,留在了祖国的西南边疆……
十四连战友戚永勤驾驶车辆由于前挡风玻璃被雾气笼罩用手擦拭时,车辆失控翻入路边的河里造成双腿受伤。
战友史可在司训队训练途中发生意外,造成左腿残疾。
他们和无数高原军人的付出换来的是西南边防建设的巩固、国家的安宁和人们的幸福,体现的是军人的本色。
五
汽车兵常年奔驰在川藏线上,饱一顿饿一顿的情况那是家常便饭,只要不当“山大王”就算幸运了。
一次,我们教练车队翻越“雀儿山”时,56号车“抛锚”在路上,我钻到发动机下面检查,拆下零件的机油滴在脸上,过往的车辆扬起的尘土铺天盖地,等我检查完出来就变成了一个活脱脱的“兵马俑”,只能看见两只眼珠滴溜溜的转……
56号车是发动机止推垫圈出了问题必须抬下发动机更换新的,在教练和五个学员的配合下我很快更换完毕使发动机恢复了正常运转。
由于天色已晚,夜间翻山越岭不安全,于是我们决定就地宿营,第二天追赶大部队。
汽车货箱装运的大米麻袋上就是我们的床铺。
听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竹卡兵站遭遇藏独土匪袭击,除兵站医生因外出给藏民看病幸免外其它人员全部牺牲。
我们从安全角度出发安排好岗哨将子弹上膛关上保险,这才进入梦乡。
六
在高原的路上有个藏族姑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车队休息,在路边小树林里三个藏族姑娘围坐在一个藏族小伙旁边吃着“糌粑”(炒熟了的青稞面)。我们凑过去看热闹,其中一个姑娘虽然脸上长了一些小疙瘩,两个脸蛋红彤彤发着“藏光”,但是她那双大大的眼睛和那张美丽的脸庞深深的吸引着我们。

都说少数民族女子粗狂野蛮不知害臊,但是这个姑娘见我们过来和她们搭讪,她总是微笑着羞涩的扭过脸去,好似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打动着我们的心。
从此藏族姑娘纯洁美丽、自然含蓄的印象改变了我对她们的认识。
那片小树林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每当我回忆起部队生活的峥嵘岁月,我就会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军旅岁月是我人生旅途的第一步也是我人生难忘而自豪的一段时光,它仿佛一直影响着我后来的工作、生活和思想观念。
人生风霜,跌宕起伏,挥不去的是这一生刻骨铭心的军旅记忆,也是我永远怀念的青春岁月。
作者简介:
王教忠:1977——1983在成都军区后勤部汽车20团服役,后在成都工作至退休。

网信达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